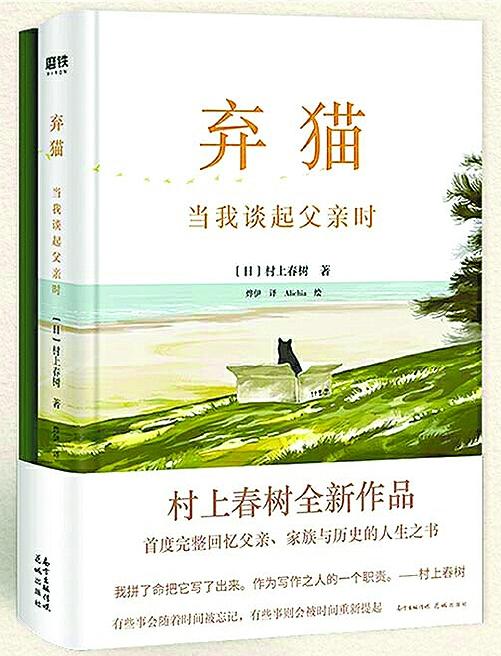無法丟棄的“貓”
對村上春樹有過一些了解的讀者都知道,他除了在諾獎陪跑多年,愛爵士樂與威士忌,他還很愛貓。村上不僅在生活中養貓,並且不只一次在作品中使用“貓”的形象,如《
尋羊冒險記》中那隻虛弱又自負的貓,《發條鳥年代記》、《1Q84》中也到處是貓的影子,在《開往中國的慢船》一文中他曾說:“我那時二十八歲,結婚以來六年的歲月已經流逝。六年的時間裡我埋葬了三隻貓,燒掉了幾個希望,把若干痛苦捲在厚毛衣裡埋進土裡。一切都在這無從掌握的大都市裡進行。”
《棄貓》與村上過往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一樣,非常輕薄,只有九十七頁,三萬字,從一起去海邊丟棄一隻貓開始,他談起了自己的父親。在一個夏日的午後,與父親騎着自行車,他坐在車後面,抱着裝貓的箱子,去到離家兩公里遠的海灘,把貓棄在海灘上並說了句“再見”,父子倆就回家了。而有趣且神奇的是,貓搶在他們前頭先到家了,一打開門,那隻“被拋棄”的貓“喵喵……”叫起來。
但這隻貓只是此書的一個引子,以棄貓事件引出了一直未曾提及的“父親”。村上用他一貫淡然的口吻,首次書寫父親的整個人生,冷靜地將自己與父親漫長的隔閡、決裂與和解轉化為文字,毫不忌諱地向讀者展示。村上春樹的父親曾是一名日軍,對戰爭之惡的深惡痛絕以及兩個不同時代的人在觀念上存在的衝突和差異,造成了村上和父親二十幾年的疏離和隔閡。
“我的父親曾是一名戰爭罪人嗎?”“他殺過普通人嗎?”“他也參加過那場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嗎?”這些隱秘的過往像包袱一樣壓迫着村上,逼迫他去不斷追尋父親的往事。決定直面歷史對村上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懷疑父親是否曾作為第二十聯隊的一員參加了南京戰役,也因此總是很抵觸去詳查他的從軍記錄。過了很久,才開始詳細調查,或者說,是在下定決心上用了很久。父親去世後,足有五年的時間,我想着一定要調查,卻也遲遲沒有落到實處。”
在村上印象中,父親幾乎不與別人講述自己在戰場的經歷,即使是和村上春樹,也只有一次提到自己在部隊處刑俘虜的中國士兵的情形,那名士兵知道自己要被處死後,沒有驚慌失措,只是一動不動地閉着眼睛,“那態度着實令人刮目相看,父親說,他恐怕到死為止,都對那名被斬首的中國士兵懷揣深深的敬意。”戰爭留給父親的“心理創傷”,一部分由村上春樹繼承了,“父親憶起用軍刀斬斷人脖子的殘忍場面,毫無疑問在幼小的我心裡烙下了鮮明的傷痕。所謂心與心的連結就是這樣,所謂的歷史就是如此。其本質就在承接這一行為——或者說儀式之中。無論其內容讓人多麼不愉快、多麼不想面對,人還是不得不接受它為自己的一部分。”
書中以真實的歷史,思考個體與集體之間的對立,尋找個體人生與世界歷史的關聯,戰爭能給一個人——一個極為平凡的默默無聞的市民的生活和精神帶來多大、多深的改變呢,這也是村上想在此書中寫的內容之一。或許對於父親而言,無論是多想割裂的戰爭記憶,還是那隻想要丟棄卻自己搶先一步跑回家的貓,都是無法丟棄的,殘酷的真相總會像貓一樣找到回家的路。但也正如村上春樹自己所說的:“我們不過是無數滴落向寬闊大地的雨滴中寂寂無名的一滴,是確實存在的,卻也是可以被替代的一滴。但這一滴雨水中,有它獨一無二的記憶。一粒雨滴有它自己的歷史,有將這歷史傳承下去的責任和義務。這一點我們不應忘記。即使它會被輕易吞沒,失去個體的輪廓,被某一個整體取代,從而逐漸消失,也正因為它會被某一個整體取代從而逐漸消失,我們才更應銘記。”
花非花